1952年,开封市委书记戴季英,自恃功高,向毛主席要官,希望担任省委书记,毛主席气道:“开除党籍,永不录用!”
新中国刚成立,戴季英被安排到河南省委常委兼开封市委书记的位置,这在当时已经是省级领导了,可他不满意。他觉得从二十年代开始,他就领导过鄂豫边区工作,在河南打仗那么多年,论资历论贡献都该上更高台阶。
在省委会议上,他开始发牢骚,讨论干部调整时,总爱插话质疑别人岗位,强调自己经验多。会后跟老部下闲聊,他抱怨省委领导决策不对,列举过去战斗细节,说组织没给他应有认可。这种不满越积越多,私下场合他联络老同志,交换看法,想影响组织决定。
1951年夏秋,河南省委搞反贪污浪费官僚主义运动,他公开反对,说运动方向不对,导致跟省委其他领导关系搞僵。省委书记潘复生主持工作,他多次批评具体措施,会议气氛越来越紧张。这种行为拖了几个月,到1951年底,他决定直接向中央反映。
写信给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直指现任省委书记工作有问题,要求调职,让他当河南省委书记。信里语言硬邦邦,直接否决组织安排,没走正常渠道,绕过省委就寄出去了。这事儿违反了组织纪律。
信送到北京,毛主席看了很生气,在批示里说共产党不需要这样的高级干部,应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永不启用。中央根据批示,很快研究决定,下发文件到河南省委执行。
中央文件下来后,1952年2月河南省委就执行了,开除戴季英党籍和公职,停掉所有职务,把他遣返回湖北原籍,让他反省。同年他被判十五年有期徒刑,关进监狱,狱里他没闹腾,保持低调,没再掺和政治事儿。
释放后,他搬到郑州河南省委北院一处房子,日子过得安静,渐渐没人提他。1984年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恢复他党籍,还给省级干部待遇,他继续在郑州住着,直到1997年11月29日病逝,活了92岁。
这事儿在党的历史上不算多见,不是因为工作出错或作风问题,而是他要官要得太直白,违反纪律。戴季英早年贡献大,在黄麻起义、根据地建设、抗日解放战争中都出力不少,但后期一封信毁了前程。不少老同志从这学到教训,调整心态,继续为建设出力。
1951年,开封市委书记戴季英给主席写信,信中攻击河南省委,自己想任省委书记,毛主席大怒:“开除公职、党籍,永不任用”!
戴季英早年曾在武汉启黄中学、武汉省立第一中学求学。1927年7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11月,戴季英参与了黄麻起义,黄麻起义失利后,他转移至黄陂县木兰山区继续坚持斗争。
1928年春季,黄麻起义武装的剩余力量被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7军,戴季英担任第7军党委委员。
同年5月,他担任中共黄麻县委书记,同时兼任共青团黄麻县委书记以及黄安县地方武装指挥部总指挥,积极发动农民开展武装斗争。
1931年6月,中共鄂豫皖省委成立,戴季英担任省委委员以及省委政治保卫局审讯科长。
1932年4月,他出任红四方面军二十五军74师政委。红四方面军在反“围剿”中失败并撤出鄂豫皖苏区后,戴季英留在鄂豫皖地区坚持斗争。
1933年4月8日,红二十五军重建时,他担任军政委兼第74师政治委员、鄂东北游击总司令,成为坚守鄂豫皖根据地斗争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他还指挥了“郭家河战斗”和“潘家河战斗”。
与此戴季英在红二十五军内部开展了肃反工作。
1934年11月,他改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并参加了长征。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牺牲后,他改任二十五军参谋长。
进入陕北后,他先后担任中共陕甘晋省委常委、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保卫局局长。
在担任保卫局局长期间,10月初,戴季英下令逮捕了刘志丹等人。
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张闻天主持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为刘志丹等人平反。
在相关会议上提到:“此次错误的主要责任,应由当时全面主持肃反工作的戴季英(彼时担任保卫局长)以及在前方负责肃反工作的聂洪钧(当时是军委主席)两位同志承担。戴季英同志在保卫局工作期间还犯下诸多严重错误,原本应受到党组织最严厉的处分,但鉴于他长期投身国内战争,为党工作多年,特决议从轻给予其最后警告处分;对聂洪钧同志则给予严重警告处分。”
1942年末,延安召开了西北高干会议。这次会议全面否定了1935年关于陕北肃反“必要性”的将陕北肃反重新定性为“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恶性发展的结果。
1960年4月,经中共中央正式批准,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指出在陕北肃反事件中,“当时中央代表派驻陕北代表团书记朱理治等同志应承担政治上的主要责任,而直接责任人是陕北保卫局长戴季英和陕北军委会主席聂洪钧”。
抗战爆发后,戴季英担任新四军第四支队副司令员(司令员为高敬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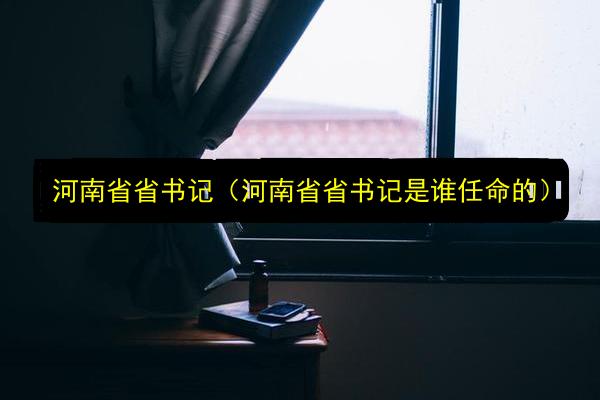
1988年的一天,已辞职赋闲的纪登奎在家里吃饭时,突然头一歪倒在了地上,家人发现他面色苍白,呼吸急促,连忙将他送到了最近的医院紧急抢救。
纪登奎1923年出生在山西武乡县一个农村家庭,从小见识过穷苦日子。1937年夏天,他十四岁就参加抗日队伍,次年春天入党。那时候,他主要在鲁西和冀鲁豫地区活动,负责组织青年参军和支援前线工作。解放战争期间,他转到豫西,先后当县委副书记和书记,领导土地改革和剿匪任务。新中国成立后,他留在河南,先在许昌地委任职,还兼军分区政委,后来去洛阳,管矿山机器厂和地委书记职务,推动工业生产恢复。六十年代,他升河南省委常委和秘书长,还短暂管商丘地区。1968年,他出任河南省革委会副主任和省委书记。次年,在党的九大上,当选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七十年代初,他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经济恢复和工业发展,同时兼北京军区政委。
那个阶段,国家经济百废待兴,他注重实际推动政策落地。1980年春天,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他提出辞去所有领导职位,会议同意了。从那以后,他转为闲居状态,三年后组织安排他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当正部级研究员,偶尔写点农村政策建议。整个一生,他从基层一步步上来,经历抗日、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设,没靠关系,全凭实干。他的作风直来直去,不爱虚的,会议上常强调结果,不容糊弄。这让他在河南和中央都留下务实名声,但也因为时代变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受到排挤,被边缘化,最终选择主动退下。很多人说,他看得远,知道有些位置坐久了不安全,选择清醒撤退的人不多见。
纪登奎的辞职不是被逼的,而是自己提的,那时候风头正紧,有人忙着往上爬,他却说不干了。在那个讲究忠诚服从的年代,这算少见操作。他的辞职信送到中央,不少人猜是不是受打击,但后来知道是自愿。退下后,他没推辞研究员职务,但也没热情,平时偶尔开会或写建议。别人想攀关系,他不见,搬回胡同老宅,过普通退休干部日子,每天买菜遛弯。生前身体有高血压和心脏隐忧,跟了好些年,但他不张扬,生活克制,按点起床吃饭散步。1988年7月13日那天,上午他还出门转了圈,晚饭时突然发病。家人发现后,立刻送医院抢救,但没来得及。他的死讯传开,老同事愣住,国务院办公室短暂慌乱,不是因为丢了个研究员,而是他曾坐副总理位置,主导经济和军政工作。九号院内部紧急商议葬礼规格,对这位离场特殊的人物,谁也不好拍板。
1975 年开国上将王平到洛阳视察,问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常香玉究竟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就让她过来为大家演一场豫剧。豫剧大师常香玉当时处境不好,不准她演出。刘建勋不好拒绝,就把常香玉请了过来。这是常香玉被打倒后第一次登台演出,从此获得解放。常香玉后来每次到北京,都要去看望王平上将,表达谢意。王平却说,不是我解放了你,是人民需要你这位艺术家。
那会儿常香玉日子过得难。之前被安了些莫名其妙的名头,戏服被收了,嗓子也快荒了,整天在家帮着做家务,手上磨出了老茧。有人来叫她去演出时,她愣在灶台边,围裙都没顾上解,眼里直发亮,又不敢信,问了三遍 “真能唱?”
去剧场的路上,她攥着临时找的素色褂子,手心直冒汗。到了后台,看见久违的化妆镜,镜上蒙着层灰,她用袖子擦了又擦,眼泪差点掉下来。上台前,王平在侧幕边站着,冲她点点头:“常先生,老百姓就爱听你唱。”
锣鼓一响,常香玉一开口,台下先是静了静,接着就爆了彩。还是那股透亮又带劲的嗓子,唱《花木兰》里 “刘大哥讲话理太偏”,一句下来,台下掌声能把屋顶掀了。她越唱越投入,之前憋的那些委屈、想念戏台的心思,全顺着唱腔撒了出来,唱到动情处,自己眼里含着泪,台下观众也跟着抹眼睛。
演完下来,常香玉握着王平的手,话都说不利索:“王将军,您是我的恩人啊。” 王平摆摆手,笑得实在:“别谢我,你往台下看看。” 台下老百姓还在拍手,有人喊 “再唱一段”,那股热乎劲,比啥都真。
后来常香玉才明白王平的话。不是谁一句话能让她登台,是她的戏早刻在老百姓心里了。当年她为抗美援朝捐飞机,唱得嗓子哑了都不停,老百姓记着这份情;她的《红娘》《白蛇传》,把日子里的喜怒哀乐唱得透亮,老百姓稀罕这份真。就算被按住几年,老百姓心里的念想没断,盼着她再开嗓呢。
她往后每次去北京看王平,都带着自己做的酱菜,坐在院里跟王平聊戏。王平总说:“艺术是给人民唱的,人民认,你就永远站得稳。” 这话常香玉记了一辈子,后来收徒弟,头一条就教 “别惦记戏台有多高,先记着台下有多少双盼着你的眼睛”。
有时候想想,真正的艺术家哪能被轻易打倒?他们的根扎在老百姓心里,就像常香玉,她的戏是唱给人民的,人民自然会把她稳稳接住。王平将军懂这个理,他没把自己当恩人,是懂了人民和艺术最实在的牵连。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